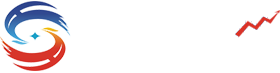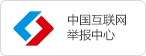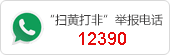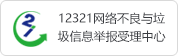周年已至,思念未减,欲将提笔泪先流。我用颤抖的双手敲下质朴的文字,打捞父亲最后的时光。
2025年农历11月22日,是父亲的周年祭日,转眼,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一年来,时光相守,念及度日,父亲的音容笑貌,父亲的谆谆教诲,几乎从没间断过,每时每刻都浮现在自己的眼前,特别是每次回老家,那老屋,那老树,还有室内陈设着父亲曾用过的那些日用品,睹物思人,仿佛感受到父亲就在眼前,依旧坐在沙发上,依旧用他那慈祥的笑容,期盼着儿女们的到来。
世事难料,人生无常,那场突如其来的噩耗,彻底撕碎了生活原有的平静,打得我措手不及——我最慈爱的父亲,竟被那人人谈之色变的癌症缠上了身。曾以为癌症离我们无比遥远,可这无情的恶魔,却悄无声息地侵入了父亲的身体,来得那样猝不及防。

2023年5月,父亲因咳嗽去县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肺炎。吊了一周消炎水,症状明显好转,我们便都放下了心。六月底回家探望二老,父亲随口提起背部隐隐作痛,说许是劳作时不小心扭到了。我听着他的描述,也没往坏处想,只附和着认定是普通扭伤,觉得吃点舒筋活络丸,再外涂些云南白药,至多一个月便能痊愈。我素来心思简单,又想着父亲身子向来硬朗,连体弱多病的母亲都一直是他在照料,何况才刚做过检查,怎么也不会往坏的方向揣测。
2025年7月底,在外工作的弟弟和弟媳回家探亲,听闻父亲背痛许久未愈,便去年8月初带着父亲去了东至人民医院做胸椎磁共振。医生看过片子后,建议再做个肺部增强CT,那一刻,一丝不安悄然爬上心头,阴霾开始笼罩在全家人的心上。“疑似肺部肿瘤”,弟弟的电话像一道晴天霹雳,我握着手机,脑子一片空白,许久都没能说出话来。当晚,我们瞒着父亲,紧急召集姊妹三家开了家庭会议,焦灼地商议着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次日,我们便带父亲住进了医院,做了全麻下的肺部切除手术,是为了做进一步病理分析。手术不过三个小时,于我们而言却漫长得如同一个世纪,所有人都坐立难安、心神不宁。当父亲被推出手术室的瞬间,积攒许久的泪水瞬间模糊了我的双眼。术后是漫长的等待,那些日子里,我日日祈祷,哪怕真是肿瘤,也盼着是良性的。可一周后的病理报告,却像一纸无情的判决书:小细胞肺癌,且已多处扩散,无法再进行手术!握着报告单,我的手止不住地颤抖,心口像是被生生撕开一道口子,疼得滴血,话到嘴边只剩哽咽,泪水汹涌而出。面对病床上满怀期待的父亲,我要如何开口,才能忍心将这残酷的真相告诉他?
可聪明的父亲,还是从一次次检查和对我们的察言观色中,隐约洞悉了真相。出院的当夜,他把我们姐弟仨叫到病床前,眼中噙着泪,却又无比坦然地开始交代后事: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该如何分配,百年后的坟冢要安在何处、该如何修葺,母亲往后的生活要怎样安顿……桩桩件件,都安排得妥帖周全。我们心如刀绞,只能强忍泪水,一遍遍安慰他:“病情是有点重,但不会危及性命,先回家养养身子,后期好好配合治疗,一定能好起来的。”
一周后,抱着一丝“或许是误诊”的侥幸,在外孙女的帮忙联络下,我们带着父亲和所有检查资料,奔赴上海瑞金医院,辗转找到了胸外科和肿瘤科的权威专家。可诊断结论与东至医院如出一辙,最后一丝希望也被彻底击碎。起初为了瞒住父亲,我们没让他和医生碰面,可转念一想,父亲满怀期待来上海求医,若是连医生的面都没见就返程,他定会无比失落。于是我们提前和专家沟通,恳请他和父亲见一面,只说后续做化疗即可,不必和盘托出病情。专家体谅我们的难处,欣然答应了。可那天从医院出来,父亲的情绪还是低落到了极点。好在在上海工作的妹妹、妹婿,还有外孙女和外孙女婿热情接待了我们。为了帮父亲疏解心情,次日,外孙女便带着父亲,在我和弟弟的陪同下,坐着观光车逛了上海滩、登了东方明珠,晚上还去看了璀璨的灯光秀。父亲的神色总算缓和了些,他感慨着,上一次来上海还是几十年前,如今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第四天,我们只能怀着怅然若失的心情,带着父亲踏上了返程的列车。
2025年8月21日,我带着父亲住进东至县人民医院,开始漫长的化疗手术。每两周一次,我们就回到这里,回到这间有消毒水气味的房间,回到这场与看不见的敌人的拉锯战。时间在这里被切割成以十四天为单位的循环,窗外的季节变换与我们无关——我们只数着化疗的次数。就这样,我们守着一袋袋将尽的药水,守着疼痛与爱交织的、往下走的日子。六次化疗结束,父亲凭借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抵抗力,挺过了干呕,挺过了疼痛,挺过了难熬的日子。也许父亲的体质对抗肿瘤的药物很敏感,加上出院后家人的细心照料,病情好转不少,每周的检查指标基本趋向正常,家人绷紧的心慢慢放松。
就这样,安稳又寻常的日子过了六个月,可2024年6月中旬,父亲接连两次晕厥,我慌忙联系医生,那句“可能是癌细胞扩散至脑部”的诊断,刚落定的一颗心,又猛地悬到了嗓子眼。六月十八日,我和妻子收拾好父亲的换洗衣物与随身日用品,将母亲安顿在姐姐家,一同赶往安庆市一一六医院。检查结果最终还是碾碎了那点侥幸——癌细胞真的侵入了父亲的大脑。医生说要放化疗同步进行,住院时长约莫四十天。我始终攥着对科学的信任,攥着那一缕不肯熄灭的希望,决定留下来陪父亲治疗,让妻子先回了家,自己请了长假,专职陪护父亲。真正住院的日子是三十七天,期间,远在外地工作的弟弟请假一周回来照料父亲。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细想,这段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三十多天,说起来不过是日历上轻得没分量的一页,可落在我和父亲身上,是在白色病房里,一分一秒、一寸一毫熬出来的时光。放疗仪器的嗡鸣像钝器的闷响,每一回看着父亲被推进那间冷得没有活气的治疗室,我的心都被一只无形的手攥得紧紧的,直到护士推门而出,那句“一切顺利”落进耳朵,胸口那团紧绷的力气才能松下来。化疗的副作用来得又凶又急,父亲的头发大把大把地往下掉,食欲一日比一日萎靡,从前能捧着一大碗米饭吃得香甜的人,如今连抿一口粥都要皱着眉,攒着力气往下咽。我便天天换着花样买他从前爱吃的东西,他吃不下,我也陪着饿,只盼着他能多吃一口,多攒一分对抗病痛的力气。父亲精神稍好的时候,我会推来轮椅,带着他在院区里慢慢走,找些轻松的话讲,想让他能暂时忘了身体里的疼。最难捱的是漫漫长夜。父亲被病痛缠得睡不着,翻来覆去地哼唧,我就起身给他掖好被角,用热毛巾擦净他额角的汗,坐在床边陪他说话。有时候他哑着嗓子说“辛苦你了”,我喉咙一紧,只能别过脸去,假装整理床头柜上的药瓶,把涌到喉头的酸意,硬生生咽回心里。我总忙着把话题往别处带,从邻里的家长里短,讲到从前的陈年旧事,直到他的呼吸慢慢沉下去,发出浅淡的鼾声。我坐在床沿的折叠椅上,看着他苍白的脸,听着监护仪规律的滴答声,一夜一夜,不敢合眼。那段日子里,我好像忘了“累”是什么感觉,忘了自己的生活,眼里心里,只有父亲的体温,和他浅浅的呼吸。七月二十四日出院那天,晴光正好,树叶滤过的碎金落在父亲的轮椅上。他的精神好了许多,还能笑着跟护士挥手道别。我推着轮椅慢慢走出医院大门,风里裹着青草与栀子的香气,那一瞬间忽然懂了,所有的熬、所有的苦,都有了归处,都值了。
在家调养的日子里,妻子极其细心地照料着父亲,亲朋好友、父亲的老同事们也纷纷登门探望。看着那些与父亲同龄的长辈,我的心便一阵阵地抽痛,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父亲这一生,从未亏欠过谁:作为有着五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对党始终忠心耿耿;作为曾经的村书记,他对群众始终尽职尽责;作为父亲,他把所有的疼爱都给了我们。这样的人,怎么就得不到命运的眷顾?苍天何其不公!

2024年11月,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先是左腿瘫痪,再是右腿也彻底失去了力气。为了宽他的心,我每天都花一两个小时给他按摩。可瘫在床上的父亲,连和病魔对抗的意志都垮了——食量越来越少,最后只能勉强喝几口水;褥疮越来越重,红得发亮的伤口慢慢裂开、腐化,看得人揪心;就连特效止痛药,也拦不住越来越凶的疼,一辈子硬气、从不说疼的父亲,到最后也熬不住,止不住地呻吟。父亲临终前的二十三个霜冷的夜,我守着一盏残灯陪着父亲,漫漫长夜的愁绪像潮水,裹着我喘不过气,心像被钝刀反复割着,连呼吸都带着疼。2024年12月22日10时24分,父亲的呼吸渐渐微弱下去,我趴在床边,一遍一遍喊着爸爸,泪水砸在他的手背上,可那点余温还是一点点散了,再也暖不回来。丧父之痛,是撕心裂肺的,是刻进骨头里的。
父亲的葬礼很圆满,一切按家乡风俗的最高标准举办。亲友们纷纷赶来送父亲最后一程,可再热闹的场面,也留不住那个总把好东西塞给我、生病时还想着护着我的人。
父亲,如今周年已至,思念分毫未减,只愿您在那边,再也没有病痛,再也没有放化疗的折磨。我们都很好,也会永远念着您。(江资文)
热线电话:0551-62620110
举报电话:0551-64376913
举报邮箱:359861220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