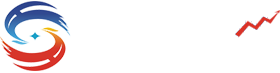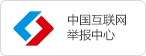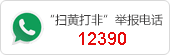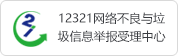陈庄是一个小小的、寂静的村庄。不知何时起,它一直寂静而孤绝地守候在那里。鱼塘边上,成片的柳树林阴沉沉地环绕着。可树没有脚,人却有脚,等到市场的风吹来,陈庄的青壮年便徙居县城、省城,甚至跑到外省去打工。
父亲成了陈庄恢复高考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人人与有荣焉,好好热闹了一场。这之后,是更长、更深的寂静。父亲毕业分配工作,也进了省城。等父亲在城里结了婚,我长大后开始往返于陈庄和省城时,村庄最热闹的活动已变成祭祖和上坟。
等我再长大一点,连着参加了数位沾亲带故的留守老人的葬礼。其中一位奶奶辈的,早没娘家亲戚可寻,而其亲生子女也已入土,进城求学务工的孙子孙女竟赶不回来,父亲便负起责任协理丧事。出殡前的守灵夜,我一边在灵堂打盹,一边透过斑斑点点泥渍沾染的窗玻璃数星星。那是万里无云的星月夜,星垂平野,月照大荒,和此前的任何一个乡村夜晚同样寂静。只是星星熠熠发光却寒气逼人,像闪亮的钢钉。开进村里的车灯光柱透明清澄,幻觉中仿佛自己在攀登高山,周遭空气清新且稀薄。第二天,我就发起了高烧,被送回省城。在那之后,我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回陈庄。偶尔在同样万里无云的星月夜,梦到村庄里的狗吠,同龄小辈们啧啧有声逗狗的叫唤,喜欢追着人跑的老母鸡踩着“红地毯”染红的指爪,空旷的屋檐和房舍,然后在午夜梦回中惊觉寂静村庄的荒诞。
很多年后,我朝着成为陈庄小辈中的第一个大学生这个目标进发时,终于再次听到村庄的消息。听罢,我哑然失笑,陈庄即将淹没在南水北调工程的浩大水脉中,而村里的留守老人和儿童,也终于像迁居他乡的亲人一样进城了——他们被安置在县城的回迁房中。再去看陈庄,原来的地方已变成大河。那时,我已是大学生。陈庄又有老人去世,但殡葬程序已大大简化,抛却乡村葬俗直接在县城的殡仪馆办追悼会。老人的子孙也天南地北赶回来,戴着口罩,和沾亲带故的我们在殡仪馆大厅沉默地面面相觑,或扑倒在停放遗体的棺椁上小声抽噎。
上坟也改道县城公墓,因墓园管理需要,园内祭扫不能大鸣大放、点燃明火,只能带束鲜花,或买些鲜果做祭品。这过程变得近似在景区的寺庙上香,一切都温文尔雅,有着体面周到的城市文明色彩。城市吞没了寂静乡村最后的绝响。
参加追悼会回程途中,父亲提议去看看曾经的陈庄。我走在白色水泥路面的河岸上,听到水闸发出秩序井然的“滴滴”放水指令声,粼粼的水波层层叠叠地荡漾开,记忆中的乡村图景漫漶不堪,却突发奇想:陈庄的子孙不像树,像水,开闸放水的指令一出,我们从善如流,四处奔涌。寂静的水脉汇入河中输送进四通八达的管道,野心勃发,在无依之地苦苦攀登,然后爆沸蒸腾,升得更高,直至完全蒸干,无处能再听到我们的名字。
这就是进城的故事,这就是寂静村庄消失的故事。陈牧遥
热线电话:0551-62620110
举报电话:0551-64376913
举报邮箱:359861220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