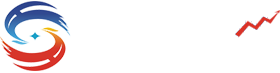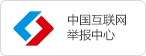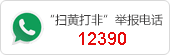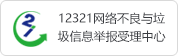当布谷鸟的啼鸣叩开封冻的岁月,蛰伏在原野的笋芽在雨水和阳光的抚慰下,一支支破土而出。“嘉蔬绿笋茎”,拥有山野园林的唐朝大诗人王维在某日踏春后,耿耿难忘的不是迷人的春色,而是那嫩笋的美味。
竹生山野,山里人最知春笋之美。在江南某山村,曾品尝过一道“腌笃鲜”。刚从山中挖回的春笋,剥皮留心,切成了滚刀块,年前腌制的腊肉切成片,配上几块五花肉、千张结,大火煮沸,小火慢“笃”,让那腊肉自带的咸味和油脂,与鲜笋的清甜渐渐融于奶白色的汤中。未至上桌,那鲜香之气已是入息沁人,及至盛放眼前浅尝一口,便被这舌尖上的春天陶醉。清朝名士李渔在其《闲情偶寄》里记述:“食笋之法多端,不能悉纪,请以两言概之,曰:素宜白水,荤用肥猪。” 山里人家简朴的“腌笃鲜”,无意契合了美食家的烹饪之诀。
我生活的小城,城中有一山,山上有一片竹林。少时,某个春日,在竹林中和小伙伴玩耍,偷偷扳了个竹笋藏在蓝布书包里带回家,虽然受了“毁了一根竹子”的责骂,但母亲的五花肉红烧竹笋的美味至今难忘。后来在这座小山的旮旯里发现一片竿如手指的小野竹林,肆无忌惮地扳了许多半尺长短的竹笋回家。母亲将这些细长的竹笋切成碎丁,与腌制的芥菜和红椒烩炒,春笋的白、芥菜的青、椒片的红,色香味俱全,酸辣脆互溶,开胃生津。多年来,母亲的这道芥菜炒笋丁,一直被我认作是佐餐小酌之佳品、春笋美食之上品。
难以忘怀的,还有外婆的腌笋尖。幼时与外婆生活在乡下,外婆的院后也有一片野生的竹林,春日竹笋疯长之时,外婆会将“吃不撤”的竹笋腌制保存。
犹记得外婆腌泡春笋的情景。阳光透过廊檐斜斜切进来,照亮外婆弓腰忙碌的身影,也照亮她指节上经年的裂口。见外婆将晒干的桂树皮与茱萸枝铺在缸底,又把对半切开用开水烫过的小笋层层码放,撒上碎盐,用大块的鹅卵石压紧。腌制的春笋出水后,十天半月后就可开吃,咸鲜脆嫩,爽口异常。如外婆当年腌泡得较多,可一直吃到夏末秋初。
到了上学的年龄,进城和父母生活。若是春天外婆进城来看我,总会装上满满一玻璃瓶的腌春笋。玻璃罐里,象牙白的笋条蜷成小小的月牙,浸泡在淡黄色的盐卤中,像是封存了一整个鲜润的乡村春天。后来我走过许多城市,吃过腊肉吊鲜的腌笃鲜,尝过用高汤煨的春笋块,品过里脊肉爆炒笋片,却再寻不到那带着外婆气息的腌春笋的鲜美。偶然在超市里发现真空包装的腌笋,打开来总觉着有一股陈腐的酸气,像是被抽走了魂魄的标本。
记得笋儿生长的春日,外婆还要煨几次春笋鸡汤。过了冬的母鸡这时节特别肥腴,在林子里慵懒地觅食。童年的我跟在外婆的身后,看她麻利地用篾篓罩住一只母鸡,又掰下几只竹笋。灶下的火苗快活地跳动,铫里的水冒出腾腾的热气。等清理干净的整鸡和切成块的春笋放进了那只被烟火熏得发黑的铫子里,外婆就将灶下的火拨旺。等铫内的水翻腾,外婆又将灶膛里的火用火叉压得小小的。这种文火慢煨出的春笋鸡汤,氤氲着我小小的童年,也熨帖着我难以忘却的记忆。
曾在皖南一处祠堂中见过一幅明代的《荐新图》,泛黄的绢帛上,春笋与青韭、鲥鱼共置红漆托盘,被郑重供奉于祖先牌位前。站在这幅《荐新图》前,看着画中历经时光难掩清新的春笋,我的脑中浮现出外婆和母亲早已消逝的身影,她们手中的春笋依是曾经的鲜新。
“苦笋鲥鱼乡味美。”春笋之美,或许是浸入了家和乡愁的滋味,才显得更为鲜香难舍吧?
又是春笋破土时,乡人送来的几根嫩笋摆在案头,一层一层地剥着笋衣,一遍又一遍地想着,该如何烹饪这春天的馈赠,慰藉我这渐被凡尘麻木的舌尖和思念。方华
热线电话:0551-62620110
举报电话:0551-64376913
举报邮箱:3598612204@qq.com